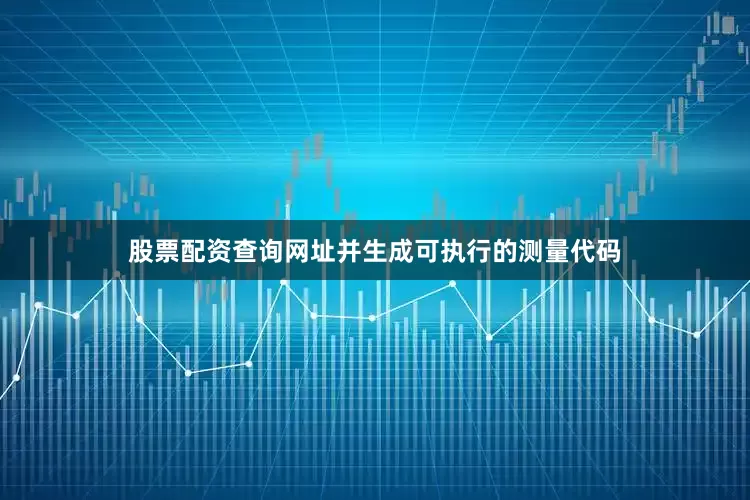目录
01逐句详解
02金芬香:深究与鉴赏
03汇评
04原文及译注
01逐句详解
第1段
汉用陈平计,间疏楚君臣。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,稍夺其权。增大怒曰:“天下事大定矣,君王自为之,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”归未至彭城,疽发背死。苏子曰:增之去善矣,不去,羽必杀增。独恨其不早耳。
详解:
1.汉用陈平计,间疏楚君臣。
汉:指汉高祖刘邦,秦末起义领袖之一,后击败项羽建立汉朝,是西汉开国皇帝。
用:采用、使用。
陈平:秦末汉初重要谋臣,早年追随项羽,后因不受重用投奔刘邦,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大功,历任惠帝、吕后、文帝时期丞相,封曲逆侯,以智谋和善于谋划离间计著称。
计:计策、计谋,此处指陈平设计离间项羽与范增关系的计谋。
间疏:“间”指离间,“疏”指疏远,合起来意为通过手段使对方君臣之间产生隔阂、关系疏远。
楚:指西楚霸王项羽建立的政权,这里代指项羽一方。
君臣:指项羽和他的大臣们,核心是项羽与范增。
译文: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,离间疏远西楚霸王项羽和他大臣之间的关系。
背景补充:楚汉相争后期,刘邦因屡败于项羽,急需削弱楚军力量。陈平了解到项羽多疑的性格,便向刘邦献计,通过贿赂楚军将士、散布谣言等方式,制造项羽对范增的怀疑,此计成为后期范增失势的直接导火索。
鉴赏:开篇简洁交代事件起因,“用计”“间疏”二词精准概括陈平的策略,为下文范增的遭遇埋下伏笔,体现了苏轼议论文“开门见山,紧扣核心”的特点。
2.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,稍夺其权。
项羽:名籍,字羽,楚国贵族后裔,秦末起义军领袖,巨鹿之战中大败秦军主力,秦亡后自称西楚霸王,分封诸侯,后在与刘邦的楚汉相争中失败,自刎于乌江。
疑:怀疑、猜忌,项羽性格中“多疑”是其重要缺陷,也是陈平离间计能成功的关键。
与汉有私:“与”指和、同,“汉”代指刘邦阵营,“有私”指有私下往来、图谋不轨的行为,这里是项羽怀疑范增暗中勾结刘邦。
稍:渐渐、逐渐,说明项羽夺取范增权力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随着疑心加深逐步进行,体现了项羽内心的犹豫与猜忌的累积。
夺:剥夺、夺取。
其权:“其”代指范增,“权”指权力,包括军事谋划权、决策权等,范增此前是项羽麾下核心谋臣,被尊为“亚父”,权力极大。
译文:项羽怀疑范增和刘邦阵营有私下往来,便逐渐剥夺了范增的权力。
人物性格分析:此句凸显项羽“多疑寡断”的性格弱点——因谣言便怀疑对自己忠心耿耿、辅佐多年的“亚父”,且“稍夺其权”的行为,既表现出他对范增仍有一丝顾虑,也暴露了他在政治决策上的盲目性,为后续范增离去埋下必然伏笔。
3.增大怒曰:“天下事大定矣,君王自为之,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”
增:指范增,项羽的主要谋臣,秦末居巢(今安徽巢湖)人,七十岁时投奔项梁,后辅佐项羽,多次建议项羽除掉刘邦,被项羽尊为“亚父”。
大怒:非常愤怒,范增一生为项氏谋划,却遭怀疑夺权,内心的忠诚与委屈化为愤怒,“大怒”既体现他的刚直,也反映出他对项羽的失望。
天下事:指争夺天下的大事,即楚汉相争的局势。
大定:基本确定、大致稳定,范增说“天下事大定”并非真认为局势已定,而是反语,暗含对项羽“失智”行为的不满——若继续任用自己,天下或可定;如今怀疑自己,天下局势已难挽回。
君王:指项羽,范增此时仍称项羽为“君王”,既体现他作为臣子的身份认知,也暗含一丝残存的尊重。
自为之:“自”指自己,“为”指处理、应对,意为“您自己去处理吧”,语气中带有失望与决绝。
愿赐骸骨:“愿”指希望,“赐骸骨”是古代大臣请求退休的委婉说法,意为“希望能允许我这把老骨头(回乡)”,体现范增年事已高且心灰意冷。
归卒伍:“归”指回到,“卒伍”原指古代军队编制(五人为伍,百人为卒),后代指乡里、家乡,意为“回到家乡去”。
译文:范增非常愤怒,说:“争夺天下的大事现在基本已经定了,君王您自己去处理吧,希望能允许我这把老骨头回到家乡去。”
范增的这句话充满复杂情感——愤怒于项羽的猜忌,失望于自己的忠诚不被认可,决绝于离开这个无法再辅佐的君主。“天下事大定矣”的反语,比直接指责更具讽刺意味,也更能体现他作为谋臣的清醒与无奈。
4.归未至彭城,疽发背死。
归:指返回故乡的途中。
未至:没有到达。
彭城:今江苏徐州,当时是西楚的都城,也是范增返回故乡的必经之地(或重要节点),此处代指“目的地”。
疽:一种恶性毒疮,多生于背部,古代医疗条件有限,疽病常为不治之症,范增因愤怒、抑郁、年老体衰,引发疽病,是其死亡的直接原因。
发背:在背部发作。
死:去世,范增的死标志着项羽阵营失去最后一位顶级谋臣,加速了项羽的败亡。
译文:范增在返回故乡的途中,还没到达彭城,背上就长了恶性毒疮,最终去世了。
背景与影响:范增之死是楚汉相争的重要转折点。此前,范增是项羽唯一能与刘邦阵营(张良、陈平)抗衡的谋臣,他的离去使项羽彻底陷入“无谋”的困境,此后项羽在军事、政治上接连失误,最终败于刘邦。苏轼在此处客观叙述范增的结局,为下文的评论铺垫情感基调——同情与惋惜。
5.苏子曰:增之去善矣,不去,羽必杀增。独恨其不早耳。
苏子:苏轼自称,“子”是古代对男子的尊称,苏轼在议论文中常用“苏子曰”引出自己的观点,增强文章的权威性与个人色彩。
之去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;“去”指离开(项羽)。
善矣:“善”指好、正确,“矣”是语气词,表肯定,意为“做得对呀”,直接表明苏轼对范增“离开”这一行为的认可。
不去:如果不离开。
羽必杀增:“羽”指项羽,“必”指必定、一定,意为“项羽必定会杀死范增”,苏轼根据项羽多疑、残暴的性格,推断出范增留下的结局,体现其对历史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。
独:只、仅仅。
恨:遗憾、惋惜,古代“恨”多为“遗憾”之意,非现代“仇恨”,此处体现苏轼对范增“离开太晚”的惋惜之情。
其不早耳:“其”代指范增,“不早”指不早点(离开),“耳”是语气词,表感叹,意为“只是遗憾他没有早点离开罢了”。
译文:苏子(苏轼)说:范增离开项羽是正确的,如果不离开,项羽必定会杀死他。只是遗憾他没有早点离开罢了。
此句是第一段的核心观点,苏轼跳出“同情范增”的传统评价,从“生存智慧”与“历史必然性”角度分析——既肯定范增“离去”的明智(避免被杀),又指出其“晚去”的不足,为下文进一步探讨“范增应何时离去”埋下伏笔,体现了苏轼议论文“辩证分析、不落俗套”的特点。
第2段
然则当以何事去?增劝羽杀沛公,羽不听,终以此失天下,当于是去耶?曰:否。增之欲杀沛公,人臣之分也,羽之不杀,犹有君人之度也,增曷为以此去哉?《易》曰:“知几其神乎!”《诗》曰:“相彼雨雪,先集维霰。”增之去,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。陈涉之得民也,以项燕、扶苏。项氏之兴也,以立楚怀王孙心。而诸侯叛之也,以弑义帝。且义帝之立,增为谋主矣。义帝之存亡,岂独为楚之盛衰,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。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。羽之杀卿子冠军也,是弑义帝之兆也。其弑义帝,则疑增之本也,岂必待陈平哉?物必先腐也,而后虫生之;人必先疑也,而后谗入之。陈平虽智,安能间无疑之主哉?
详解:
1.然则当以何事去?
然则:“然”指“这样(范增应离开)”,“则”表转折,意为“既然这样,那么”,承接上文苏轼“增之去善矣”的观点,引出下文对“离去时机”的探讨,起到过渡作用。
当以何事去:“当”指应当、应该,“以”指因为、凭借,“何事”指什么事情,意为“那么范增应当因为什么事情离开呢?”,以设问开篇,引发读者思考,推动文章层层深入。
译文:既然这样,那么范增应当因为什么事情离开呢?
鉴赏:此句是第二段的“总起设问”,苏轼不直接给出答案,而是通过提问引导读者跟随自己的思路分析,使文章结构更具逻辑性,也增强了论述的互动性与说服力。
2.增劝羽杀沛公,羽不听,终以此失天下,当于是去耶?
劝:劝说、建议,范增多次在关键节点(如鸿门宴)建议项羽杀刘邦,是其作为谋臣的核心策略之一。
沛公:指刘邦,刘邦早年在沛县(今江苏沛县)起兵,故称“沛公”,是项羽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。
不听:不听取(建议),项羽因“妇人之仁”“骄傲自大”,多次拒绝范增杀刘邦的建议,这是他最终失天下的重要原因。
终以此失天下:“终”指最终,“以”指因为(这件事,即不杀刘邦),“失天下”指失去争夺天下的机会、最终失败,苏轼此处先提出传统观点——“范增应在项羽不杀刘邦时离去”,为后文反驳做铺垫。
当于是去耶:“当”指应当,“于”指在,“是”指这个时候(项羽不杀刘邦时),“耶”是语气词,表疑问,意为“(范增)应当在这个时候离开吗?”。
译文:范增劝说项羽杀刘邦,项羽不听取,最终因为这件事失去了天下,(范增)应当在这个时候离开吗?
背景补充:鸿门宴是范增劝项羽杀刘邦的关键事件。公元前206年,刘邦入关后驻军霸上,项羽率大军进驻鸿门,范增认为“沛公居山东时,贪于财货,好美姬。今入关,财物无所取,妇女无所幸,此其志不在小”,多次示意项羽杀刘邦,还安排项庄舞剑助兴,欲借机刺杀,但项羽因刘邦的示弱与项伯的劝说而放弃,最终让刘邦逃脱。传统观点多认为,范增此时应认清项羽的“不可辅”,选择离去,苏轼在此先引用这一观点,为后文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做对比。
3.曰:否。
曰:说,此处是苏轼对前文设问的回答,简洁明了,态度坚决。
否:不、不是,直接否定“范增应在项羽不杀刘邦时离去”的传统观点,引发读者好奇——苏轼认为的“正确时机”究竟是什么时候?
译文:(苏轼)说:不是。
点评:一个“否”字,干脆利落,打破传统认知,体现苏轼议论文“敢于质疑、独抒己见”的特点,为下文阐述自己的核心观点(范增应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去)做好铺垫。
4.增之欲杀沛公,人臣之分也,羽之不杀,犹有君人之度也,增曷为以此去哉?
增之欲杀沛公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;“欲”指想要、打算,意为“范增想要杀刘邦”。
人臣之分也:“人臣”指臣子,“分”指职责、本分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是作为臣子的本分”,苏轼认为,范增作为项羽的谋臣,为君主铲除潜在威胁(刘邦)是应尽的职责,不能因君主不采纳就离去,否则不符合“忠臣”的本分。
羽之不杀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意为“项羽不杀刘邦”。
犹有君人之度也:“犹”指还、仍然,“君人”指君主,“度”指度量、胸襟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说明他还有作为君主的胸襟”,苏轼客观评价项羽——不杀刘邦虽为战略失误,但从“君主度量”角度看,并非完全不可取(避免了“滥杀功臣/对手”的恶名),这一评价跳出“成败论英雄”的局限,更显客观。
增曷为以此去哉:“曷为”即“为何”“为什么”,“以”指因为,“此”指这件事(项羽不杀刘邦),“哉”是语气词,表疑问,意为“范增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离开呢?”。
译文:范增想要杀刘邦,是作为臣子的本分;项羽不杀刘邦,说明他还有作为君主的胸襟,范增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离开呢?
观点分析:苏轼在此处从“臣子本分”与“君主度量”两个维度反驳传统观点——既肯定范增“劝杀刘邦”的合理性(尽忠),也不否定项羽“不杀刘邦”的正面意义(有度量),因此认为“不杀刘邦”不足以成为范增离去的理由。这种辩证分析,避免了对历史人物的“非黑即白”评价,体现了苏轼深厚的历史洞察力。
5.《易》曰:“知几其神乎!”
《易》:指《周易》,又称《易经》,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,包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与辩证思维,常被用于分析事物发展规律与趋势。
知几其神乎:“知”指察觉、知道,“几”指事物发展的微小征兆、苗头,“其”表推测,“神”指神明、高明(达到神奇的境界),意为“能察觉事物发展的微小征兆,大概就是高明到神明的境界了吧!”,苏轼引用《周易》的话,是为了强调“把握时机的重要性”——范增应在“征兆显现时”离去,而非等到矛盾激化。
译文:《周易》说:“能察觉事物发展的微小征兆,大概就是高明到神明的境界了吧!”
引用目的:引用儒家经典增强文章的理论依据与权威性,同时为下文提出“范增应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去”的观点做理论铺垫——杀卿子冠军就是“项羽将弑义帝”的“微小征兆”,范增若能“知几”,就应此时离去。
6.《诗》曰:“相彼雨雪,先集维霰。”
《诗》:指《诗经》,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,儒家经典之一,常被用于比喻、说理,增强文章的文学性与说服力。
相彼雨雪,先集维霰:“相”指看、观察,“彼”指那(雨雪),“雨雪”指下雪,“先集”指先聚集、先降落,“维”是助词,无实义,“霰”指小雪珠(雪下之前先降落的白色小冰粒),意为“看那下雪的过程,总是先聚集降落小雪珠(然后才下大雪)”,苏轼用“霰(小雪珠)”比喻“杀卿子冠军(小征兆)”,用“雨雪(大雪)”比喻“弑义帝(大事件)”,说明“大事件的发生必有小征兆”。
译文:《诗经》说:“看那下雪的过程,总是先聚集降落小雪珠(然后才下大雪)。”
比喻解读:此句与上句《周易》的引用呼应,进一步强调“知几”的重要性——事物的发展是渐进的,大矛盾的爆发必有小苗头,范增作为顶级谋臣,应能从“杀卿子冠军”这一“小雪珠”中,预见“弑义帝”这一“大雪”,从而及时离去。引用《诗经》使抽象的“征兆论”变得具体形象,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与感染力。
7.增之去,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。
增之去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意为“范增的离开”。
当于:应当在(某个时候)。
羽杀卿子冠军时也:“羽”指项羽,“卿子冠军”指宋义(“卿子”是对人的尊称,“冠军”指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,位在诸将之上,是当时楚军的最高统帅),“时”指时候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应当在项羽杀死卿子冠军的时候”,此句是苏轼在第二段提出的核心观点——明确范增“离去的正确时机”。
译文:范增的离开,应当在项羽杀死卿子冠军的时候。
背景补充:卿子冠军宋义的死因:公元前207年,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、项羽为次将、范增为末将,率军救赵(当时赵国被秦军围困于巨鹿)。宋义行至安阳(今山东曹县东南)后,畏缩不前,滞留四十六天,项羽以“宋义与齐谋反楚”为由,假托楚怀王命令杀死宋义,自立为上将军,随后率楚军破釜沉舟,大败秦军于巨鹿。苏轼认为,“杀宋义”是项羽“挑战义帝权威”的开始,也是“后续弑义帝”的征兆。
点评:此句是第二段的“观点核心”,苏轼跳出传统的“鸿门宴”视角,从“项氏与义帝的关系”这一更深层的政治矛盾入手,指出“杀卿子冠军”是范增离去的关键节点,体现了他“见微知著、透过现象看本质”的历史眼光。
8.陈涉之得民也,以项燕、扶苏。
陈涉:即陈胜,秦末农民起义领袖,公元前209年与吴广在大泽乡起义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导者,起义后建立“张楚”政权,后失败被杀。
之得民也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“得民”指得到百姓的拥护、支持,“也”表停顿,意为“陈涉得到百姓的拥护”。
以项燕、扶苏:“以”指凭借、借助,“项燕”是楚国名将,项羽的祖父,秦灭楚时战死,在楚地百姓中威望极高;“扶苏”是秦始皇长子,因反对秦始皇暴政被派往上郡监军,后被赵高、胡亥伪造诏书赐死,百姓多同情他,意为“是凭借(借用)项燕和扶苏的名义(威望)”。
译文:陈涉得到百姓的拥护,是凭借(借用)项燕和扶苏的名义(威望)。
苏轼以陈涉“借名人名义得民心”为例,为下文论述“项氏借义帝名义兴”做类比——说明“借助权威名义”是乱世中“得民心、兴势力”的关键策略,从而为“义帝对项氏的重要性”奠定论证基础。
9.项氏之兴也,以立楚怀王孙心。
项氏:指项梁、项羽叔侄领导的势力,是秦末起义军的重要力量。
之兴也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“兴”指兴起、兴盛,“也”表停顿,意为“项氏势力的兴起”。
以立楚怀王孙心:“以”指因为、凭借,“立”指拥立,“楚怀王孙心”指楚怀王的孙子熊心(楚怀王是战国时期楚国君主,被秦国欺骗囚禁,客死秦国,楚地百姓对其极为同情),秦末项梁起义后,为借助楚国旧贵族威望,找到流落民间、为人牧羊的熊心,拥立他为楚怀王,后项羽尊其为“义帝”,意为“是因为拥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”。
译文:项氏势力的兴起,是因为拥立了楚怀王的孙子熊心(为楚怀王)。
背景补充:项梁拥立熊心的原因:秦灭楚后,楚地百姓对秦国怨恨极深,且流传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的预言。项梁作为楚国贵族后裔,拥立楚怀王之孙熊心,既能借助“楚怀王”的旧威望凝聚楚地百姓,又能以“复兴楚国”为旗帜吸引其他反秦势力,从而快速壮大项氏力量。苏轼强调这一点,是为了说明“义帝是项氏兴起的核心政治符号”。
此句与上句“陈涉之得民也,以项燕、扶苏”形成类比,共同证明“借权威名义兴势力”的规律,进而引出下文“项氏因弑义帝而失诸侯”的论述,使论证链条更完整。
10.而诸侯叛之也,以弑义帝。
而:表转折,意为“但是”,承接上文“项氏因立义帝而兴”,转而论述“项氏因弑义帝而衰”,形成对比。
诸侯叛之也:“诸侯”指项羽分封的各路诸侯(如刘邦、英布、彭越等),“叛之”指背叛项羽,“也”表停顿,意为“但是各路诸侯背叛项羽”。
以弑义帝:“以”指因为,“弑”指臣杀君、子杀父(古代严格的伦理概念,“弑”比“杀”更具贬义,强调“以下犯上”的不义),“义帝”即熊心(项羽分封诸侯后,尊熊心为“义帝”,并将其迁往长沙郴县,后派英布将其杀害),意为“是因为(项羽)杀害了义帝”。
译文:但是各路诸侯背叛项羽,是因为(项羽)杀害了义帝。
影响分析:项羽弑义帝的行为,严重违背了“君臣伦理”,也打破了他“复兴楚国”的政治承诺,使各路诸侯看清其“残暴、不义”的本质,纷纷倒向刘邦。例如,刘邦在得知义帝被杀后,立即为义帝发丧,号召诸侯共同讨伐项羽,得到了广泛响应。苏轼在此处强调“弑义帝”是项氏失势的关键,为下文论述“范增与义帝的祸福相依”做铺垫。
11.且义帝之立,增为谋主矣。
且:况且、而且,表递进,进一步强调范增与义帝的关系,增强论证力度。
义帝之立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意为“义帝的拥立”。
增为谋主矣:“增”指范增,“为”指是、作为,“谋主”指主要谋划者、核心谋士,“矣”表肯定,意为“范增是(拥立义帝的)主要谋划者”。
译文:况且拥立义帝这件事,范增是主要谋划者。
此句将范增与义帝的关系从“间接关联”变为“直接关联”——范增不仅是项氏的谋臣,更是“立义帝”的核心推动者,因此“义帝的存亡”与“范增的祸福”必然紧密相连,为下文“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”的结论做铺垫。
12.义帝之存亡,岂独为楚之盛衰,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。
义帝之存亡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意为“义帝的生存与死亡”。
岂独为楚之盛衰:“岂独”指难道仅仅、何止,“为”指关系到、影响,“楚”指项氏建立的西楚政权,“盛衰”指兴盛与衰败,意为“难道仅仅关系到西楚政权的兴盛与衰败吗?”,用反问语气强调义帝存亡的影响范围更广。
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:“亦”指也、还,“增之”指范增的,“所与同祸福”指“与之(义帝)共同承受祸福的(事情)”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也关系到范增的祸福,(范增)是与义帝共同承受祸福的”。
译文:义帝的生存与死亡,难道仅仅关系到西楚政权的兴盛与衰败吗?也关系到范增的祸福,范增是与义帝共同承受祸福的。
13.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。
未有:没有(这样的情况)。
义帝亡:义帝死亡。
而增独能久存者也:“而”表转折,“增”指范增,“独能”指唯独能够、单独能够,“久存”指长久存活,“者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而范增唯独能够长久存活的情况”。
译文:从来没有义帝死亡了,而范增唯独能够长久存活的情况。
此句是对上文“义帝与范增祸福相依”的进一步强化,用“未有……者也”的绝对句式,强调“义帝亡则范增必不能久存”的历史必然性,使“范增应在义帝将亡前离去”的观点更具说服力。
14.羽之杀卿子冠军也,是弑义帝之兆也。
羽之杀卿子冠军也: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意为“项羽杀死卿子冠军这件事”。
是:这、这个(事情)。
弑义帝之兆也:“弑义帝”指杀害义帝,“之兆”指征兆、苗头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是(项羽)杀害义帝的征兆”。
译文:项羽杀死卿子冠军这件事,是(他)杀害义帝的征兆。
苏轼为何认为“杀卿子冠军”是“弑义帝”的征兆?因为卿子冠军宋义是义帝亲自任命的上将军,代表义帝的权威。项羽杀死宋义,本质是“以下犯上”,挑战义帝的统治权——既然项羽敢杀义帝任命的最高将领,就必然敢杀义帝本人。这一解读,将“杀宋义”与“弑义帝”从“孤立事件”变为“因果关联”,进一步论证了“范增应在此时离去”的合理性。
15.其弑义帝,则疑增之本也,岂必待陈平哉?
其弑义帝:“其”指项羽,“弑义帝”指杀害义帝。
则疑增之本也:“则”指就是、便是,“疑增”指怀疑范增,“之本”指“根源、根本原因”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就是(项羽)怀疑范增的根源”。
岂必待陈平哉:“岂必”指难道一定、何必,“待”指等待、依靠,“陈平”指陈平的离间计,“哉”是语气词,表反问,意为“难道一定要等待陈平(的离间计)吗?”。
译文:项羽杀害义帝,就是(他)怀疑范增的根源,难道一定要等待陈平(的离间计)吗?
此句打破“陈平离间计是项羽疑范增的根本原因”的传统认知,指出“弑义帝”才是“疑增之本”——因为范增是“立义帝”的谋主,项羽杀害义帝后,必然会担心范增因“不满弑帝”而背叛自己,这种怀疑是“内生的、必然的”,陈平的离间计只是“外在诱因”,加速了矛盾的爆发。这一观点体现了苏轼“透过表象看本质”的历史洞察力,使论证更具深度。
16.物必先腐也,而后虫生之;人必先疑也,而后谗入之。
物必先腐也,而后虫生之:“物”指物体、东西,“必”指必定、一定,“先腐”指先腐烂,“也”表停顿,“而后”指然后、之后,“虫生之”指虫子在上面滋生,意为“物体必定是先腐烂了,然后虫子才会在上面滋生”,用“物腐生虫”的自然现象比喻“人先有疑心,而后谗言才能生效”。
人必先疑也,而后谗入之:“人”指人(此处特指项羽),“必先疑”指必定先有疑心,“也”表停顿,“而后”指然后,“谗入之”指谗言(此处指陈平的离间计)能进入(他的耳朵)、能生效,意为“人必定是先有了疑心,然后谗言才能进入(他的心中)、才能生效”。
译文:物体必定是先腐烂了,然后虫子才会在上面滋生;人必定是先有了疑心,然后谗言才能进入(他的心中)、才能生效。
比喻论证:此句是经典的比喻论证,将抽象的“君臣信任与离间计的关系”转化为具体的“物腐生虫”现象,通俗易懂且极具说服力。苏轼用这一比喻,进一步证明“项羽疑范增的根本原因是内生的(因弑义帝而疑增),而非外在的(陈平离间计)”,使前文的观点更易被读者理解和接受。
17.陈平虽智,安能间无疑之主哉?
陈平虽智:“陈平”指陈平,“虽”指虽然,“智”指聪明、有智谋,肯定陈平的个人能力,为下文的反问做铺垫。
安能:“安”指怎么、哪里,“能”指能够,意为“怎么能够”,用反问语气强调“不能”。
间无疑之主哉:“间”指离间,“无疑之主”指没有疑心的君主(此处指若项羽对范增无内生疑心),“哉”是语气词,表反问,意为“离间没有疑心的君主呢?”。
译文:陈平虽然聪明有智谋,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心的君主呢?
论证收尾:此句是第二段的论证收尾,通过反问强化“内生疑心是关键”的观点——若项羽对范增无因“弑义帝”而生的疑心,即便陈平有再高的智谋,也无法离间二人。这一结论既回应了第一段“汉用陈平计,间疏楚君臣”的事件,又深化了“范增应在杀卿子冠军时离去”的核心观点,使第二段的论证形成完整闭环。
第3段
吾尝论义帝,天下之贤主也:独遣沛公入关,不遣项羽,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,而擢以为上将,不贤而能如是乎?羽既矫杀卿子冠军,义帝必不能堪。非羽弑帝,则帝杀羽,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增始劝项梁立义帝,诸侯以此服从,中道而弑之,非增之意也,夫岂独非其意,将必力争而不听也。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,羽之疑增,必自是始矣。
详解:
1.吾尝论义帝,天下之贤主也:
吾:我,苏轼自称,用第一人称“吾”,使论述更具个人色彩与真诚感。
尝:曾经,表明“论义帝为贤主”是苏轼此前就有的观点,非临时立论,增强观点的稳定性。
论:评论、论断。
义帝:即熊心,楚怀王之孙,项梁拥立为楚怀王,项羽尊为义帝,后被项羽杀害。
天下之贤主也:“天下”指天下人、世间,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“贤主”指贤明的君主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是天下公认的贤明君主”,开篇直接亮出对义帝的评价,为下文论证“义帝贤明”做总起。
译文:我曾经评论义帝,认为他是天下公认的贤明君主:
鉴赏:此句以“吾尝论”开篇,语气肯定,直接确立义帝“贤主”的形象,打破传统认知中“义帝是项氏傀儡”的片面看法,为下文分析“项羽弑义帝的不义”与“范增与义帝的关联”提供前提。
2.独遣沛公入关,不遣项羽,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,而擢以为上将,不贤而能如是乎?
独遣沛公入关,不遣项羽:“独遣”指单独派遣、只派遣,“沛公”指刘邦,“入关”指进入关中(函谷关以西,是秦朝都城咸阳所在地,秦亡后成为战略要地),“不遣”指不派遣,意为“(义帝)单独派遣刘邦入关,却不派遣项羽”。背景补充:秦末,义帝与诸将约定“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”,他派刘邦率军西进关中,派宋义、项羽率军北上救赵,不派项羽入关,一是因为项羽性格残暴(此前曾屠襄城),恐入关后伤害百姓;二是为了平衡项氏势力,体现其政治远见。
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:“识”指识别、发现(人才),“卿子冠军”指宋义,“于稠人之中”指在众人之中、在普通将领之中(“稠人”指众多的人),意为“在众多将领中发现了卿子冠军宋义”。
而擢以为上将:“而”表顺承,“擢”指提拔、提升,“以为”指“以(之)为”,即“把(他)任命为”,“上将”指最高将领、上将军,意为“并且把他提拔为上将军”。
不贤而能如是乎:“不贤”指不贤明,“而”表转折,“能如是”指能做到这样(指“独遣沛公入关”“擢宋义为上将”),“乎”是语气词,表反问,意为“不贤明的君主能做到这样吗?”。
译文:(义帝)单独派遣刘邦入关,却不派遣项羽;在众多将领中发现了卿子冠军宋义,并且把他提拔为上将军,不贤明的君主能做到这样吗?
苏轼通过两个具体事例论证义帝的“贤明”:一是“用人得当”——派刘邦入关(刘邦入关后“约法三章”,深得民心),不派项羽(避免残暴行径);二是“识才善任”——在众人中提拔宋义为上将(虽然后来宋义畏战被杀,但义帝“识才”的眼光本身值得肯定)。用反问句收尾,增强了“义帝贤明”的论证力度,也为下文“项羽弑贤主”的不义性做铺垫。
3.羽既矫杀卿子冠军,义帝必不能堪。
羽:指项羽。
既:已经、……之后,指项羽杀死宋义之后。
矫杀:“矫”指假托(名义)、伪造,“杀”指杀害,意为“假托(义帝的)命令杀害(宋义)”(项羽杀宋义时,宣称“宋义与齐谋反楚”,假托义帝命令将其处死)。
卿子冠军:指宋义,义帝亲自任命的上将军,代表义帝的权威。
义帝必不能堪:“义帝”指熊心,“必”指必定、一定,“不能堪”指不能忍受、无法容忍(“堪”指忍受、承受),意为“义帝必定不能忍受(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)”。
译文:项羽已经假托(义帝的)命令杀害了卿子冠军宋义,义帝必定不能忍受(这种行为)。
矛盾分析:此句点明“项羽杀宋义”与“义帝忍无可忍”之间的矛盾——宋义是义帝的“上将”,杀宋义就是“挑战义帝权威”,贤明的义帝必然不会容忍这种“以下犯上”的行为,为下文“非羽弑帝,则帝杀羽”的结论做铺垫。
4.非羽弑帝,则帝杀羽,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
非……则……:表选择关系,意为“不是……就是……”,强调两种结果的必然性,无第三种可能。
羽弑帝:项羽杀害义帝。
帝杀羽:义帝杀死项羽。
不待智者而后知也:“不待”指不需要等待、不必依靠,“智者”指聪明的人,“而后知”指然后才知道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不需要依靠聪明的人(分析)就能知道(这个结果)”。
译文:不是项羽杀害义帝,就是义帝杀死项羽,不需要依靠聪明的人(分析)就能知道(这个结果)。
苏轼根据“项羽挑战权威”与“义帝贤明且不能忍”的前提,推导出“二者必存一”的必然结果,说明“项羽弑义帝”是“主动消除威胁”的必然选择,而非偶然行为。这一推导,进一步强化了“杀宋义是弑义帝之兆”的观点,也为下文“范增应预见此结果”做铺垫。
5.增始劝项梁立义帝,诸侯以此服从,中道而弑之,非增之意也,夫岂独非其意,将必力争而不听也。
增始劝项梁立义帝:“增”指范增,“始”指起初、最初,“劝”指劝说,“项梁”指项羽的叔父,秦末项氏势力的早期领袖,后在定陶之战中被秦军击败战死,“立义帝”指拥立熊心为楚怀王(后尊为义帝),意为“范增起初劝说项梁拥立义帝”。
诸侯以此服从:“诸侯”指各路反秦诸侯,“以此”指因为这件事(拥立义帝),“服从”指服从(项氏的领导),意为“各路诸侯因为(项氏拥立义帝)而服从(项氏的领导)”,呼应第二段“项氏之兴也,以立楚怀王孙心”的观点。
中道而弑之:“中道”指中途、半路(指义帝还在位时),“而”表转折,“弑之”指杀害他(义帝),意为“(项羽)却在中途杀害了义帝”。
非增之意也:“非”指不是,“增之意”指范增的本意、意愿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这不是范增的本意”。
夫岂独非其意:“夫”是发语词,无实义,“岂独”指难道仅仅、何止,“非其意”指不是他的本意,意为“难道仅仅不是他的本意吗?”,用反问语气强调范增的态度不仅是“不赞同”,更是“反对”。
将必力争而不听也:“将”指必定、一定,“必力争”指必定极力劝谏、反对,“而不听”指(项羽)却不听取(他的劝谏)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(范增)必定会极力劝谏(项羽不要杀义帝),但项羽却不听取”。
译文:范增起初劝说项梁拥立义帝,各路诸侯因为(这件事)而服从(项氏的领导);(项羽)却在中途杀害了义帝,这不是范增的本意。难道仅仅不是他的本意吗?(范增)必定会极力劝谏(项羽不要杀义帝),但项羽却不听取。
此句既体现苏轼对范增的“同情”——范增是“立义帝”的谋主,却无力阻止“弑义帝”的行为,忠诚不被采纳;又从“范增力争而项羽不听”的细节,进一步论证“项羽疑增的必然性”——项羽不听范增的劝谏,杀害范增拥立的义帝,必然会担心范增因此不满,从而产生疑心,为下文“羽之疑增,必自是始矣”的结论做铺垫。
6.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,羽之疑增,必自是始矣。
不用其言:“不用”指不采用、不听取,“其言”指范增的话(劝谏不要杀义帝的话),意为“(项羽)不听取范增的劝谏”。
而杀其所立:“而”表递进,“杀”指杀害,“其所立”指范增所拥立的(义帝),意为“并且杀害了范增所拥立的义帝”。
羽之疑增:“羽”指项羽,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“疑增”指怀疑范增,意为“项羽对范增的怀疑”。
必自是始矣:“必”指必定、一定,“自”指从,“是”指这个时候(项羽不听范增劝谏、杀害义帝的时候),“始”指开始,“矣”表肯定,意为“必定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”。
译文:(项羽)不听取范增的劝谏,并且杀害了范增所拥立的义帝,项羽对范增的怀疑,必定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此句是第三段的核心结论,苏轼明确指出“项羽疑范增的开始时间”——不是陈平离间计之时,而是“不听增言、弑增所立义帝”之时。这一结论,既呼应了第二段“其弑义帝,则疑增之本也”的观点,又通过“不用其言”“杀其所立”两个具体行为,使“疑增之本”更具细节支撑,进一步强化了“范增应在杀卿子冠军时离去(预见弑义帝与疑增)”的核心观点,使全文论证更连贯、更具说服力。
第4段
羽杀卿子冠军,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,君臣之分未定也。为增计者,力能诛羽则诛之,不能则去之,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?增年已七十,合则留,不合则去,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,而欲依羽以成功名。陋矣!虽然,增,高帝之所畏也。增不去,项羽不亡。呜呼!增亦人杰也哉!
详解:
1.羽杀卿子冠军,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,君臣之分未定也。
羽杀卿子冠军:指项羽杀死卿子冠军宋义这件事,承接上文,明确讨论的时间节点。
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:“增”指范增,“与”指和、同,“羽”指项羽,“比肩”指并肩、地位平等(“比”指并列),“而”表修饰,“事义帝”指侍奉义帝(“事”指侍奉、辅佐),意为“范增和项羽是并肩侍奉义帝的(臣子)”。
君臣之分未定也:“君臣之分”指“君主与臣子的名分”(此处指项羽与范增之间的君臣关系),“未定”指没有确定、尚未确立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(范增与项羽之间的)君臣名分还没有确定”。
译文:在项羽杀死卿子冠军宋义的时候,范增和项羽是并肩侍奉义帝的(臣子),(他们之间的)君臣名分还没有确定。
此句是苏轼为范增“谋划离去”的核心前提——既然范增与项羽“比肩事义帝”,而非“明确的君臣”,范增就没有“必须辅佐项羽”的义务,因此拥有“诛羽”或“离去”的选择权。这一前提,打破了“范增是项羽臣子,必须忠诚到底”的传统认知,为下文“为增计者”的建议提供了合理性。
2.为增计者,力能诛羽则诛之,不能则去之,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?
为增计者:“为”指替、给,“增”指范增,“计”指谋划、考虑(策略),“者”指……的人(此处指“替范增谋划的人”,即苏轼自己),意为“替范增谋划(策略)的话”。
力能诛羽则诛之:“力能”指有能力、有力量,“诛羽”指杀死项羽(因项羽杀宋义、将弑义帝,是“不义之人”,故“诛羽”有“诛杀不义”的正当性),“则”指就,“诛之”指杀死他(项羽),意为“如果有能力杀死项羽,就杀死他”。
不能则去之:“不能”指(如果)没有能力(杀死项羽),“则”指就,“去之”指离开他(项羽),意为“如果没有能力,就离开他”。
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:“岂不”指难道不是、岂不是,“毅然”指坚决、果断的样子,“大丈夫”指有志向、有气节、行事果断的男子(古代对理想男性人格的赞美),“也哉”是语气词,表感叹与肯定,意为“难道不是果断的大丈夫吗?”。
译文:替范增谋划(策略)的话,如果(他)有能力杀死项羽,就杀死他;如果没有能力,就离开他,(这样做)难道不是果断的大丈夫吗?
苏轼在此处为范增提出“极端但合理”的两种选择——“诛羽”(因项羽不义,诛之是“除暴”)或“去之”(因无力诛羽,离去是“避祸”),并以“毅然大丈夫”赞美这两种选择,反衬范增“不离去”的“不果断”,为下文“陋矣”的评价做铺垫。同时,“诛羽”的建议虽极端,但体现了苏轼对“义”的重视——在“不义”面前,不应因“私恩”(项氏的重用)而放弃“公义”(阻止弑帝、除暴)。
3.增年已七十,合则留,不合则去,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,而欲依羽以成功名。陋矣!
增年已七十:“增”指范增,“年已七十”指年龄已经七十岁了,强调范增“年事已高”,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,应及时做出选择,增强“明去就之分”的紧迫性。
合则留,不合则去:“合”指(与项羽)志同道合、相处融洽,“则”指就,“留”指留下(辅佐);“不合”指(与项羽)志向不同、相处不融洽,“则”指就,“去”指离开,意为“(与君主)志同道合就留下,不合就离开”,这是苏轼提出的“臣子择主”的基本原则,体现了古代“良禽择木而栖”的价值观。
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:“不以此时”指不在这个时候(项羽杀宋义、君臣名分未定的时候),“明”指明辨、明确,“去就之分”指“离开”与“留下”的界限、抉择(“去就”是古代臣子对待君主的核心抉择),意为“不在这个时候明辨'离开’与'留下’的抉择”。
而欲依羽以成功名:“而”表转折,“欲”指想要、打算,“依羽”指依靠项羽,“以”指来、用来,“成功名”指成就功业与名声,意为“却想要依靠项羽来成就自己的功业与名声”。
陋矣:“陋”指见识浅陋、不明事理(此处是苏轼对范增“不离去”的批评,但语气委婉,不含恶意,更多是“惋惜”),“矣”是语气词,表感叹,意为“(这真是)见识浅陋啊!”。
译文:范增年龄已经七十岁了,(臣子与君主)志同道合就留下,不合就离开,(他)不在这个时候明辨“离开”与“留下”的抉择,却想要依靠项羽来成就自己的功业与名声,(这真是)见识浅陋啊!
此句是苏轼对范增的直接评价——“陋矣”,但批评中饱含惋惜:范增年已七十,本应“明去就”,却因“欲依羽成功名”而错失时机,最终落得“受疑而死”的结局。这一评价,既指出了范增的“不足”(见识浅陋),也体现了苏轼对“老臣求功名而失智”的理解与同情,避免了“苛责古人”的生硬感。
4.虽然,增,高帝之所畏也。
虽然:“虽”指虽然(承认前文范增“陋矣”的不足),“然”指这样(范增有不足),意为“虽然(范增有这样的不足)”,表转折,引出对范增的肯定评价,使论述更辩证。
增:指范增。
高帝之所畏也:“高帝”指汉高祖刘邦(刘邦死后的庙号,此处用“高帝”,体现对刘邦的尊重,也说明是“事后评价”),“之”是助词,无实义,“所畏”指“所畏惧的人”,“也”表判断,意为“(范增)是汉高祖刘邦所畏惧的人”。
译文:虽然(范增有这样的不足),但范增是汉高祖刘邦所畏惧的人。
苏轼引用“高帝畏增”这一史实,来肯定范增的“才能与重要性”——连刘邦这样的开国君主都畏惧范增,说明范增的智谋对项羽阵营至关重要,为下文“增不去,项羽不亡”的观点做铺垫。同时,“虽然”的转折,使评价更全面——既指出范增的“不足”,又肯定他的“价值”,避免了“非黑即白”的评价。
5.增不去,项羽不亡。
增不去:“增”指范增,“不去”指不离开(项羽),意为“如果范增不离开项羽”。
项羽不亡:“项羽”指西楚霸王项羽,“不亡”指不会灭亡、不会失败,意为“项羽就不会灭亡(失败)”。
译文:如果范增不离开项羽,项羽就不会灭亡(失败)。
影响评价:此句是对范增“历史地位”的高度肯定——范增的存在与否,直接关系到项羽的存亡。这一评价并非夸张:范增若在,会继续为项羽谋划,阻止项羽的诸多失误(如鸿门宴放刘邦、分封诸侯失当等),刘邦阵营也难以轻易击败楚军。苏轼通过这一评价,进一步强化了“范增是英杰”的观点,也使前文“恨其不早去”的惋惜之情更浓厚。
6.呜呼!增亦人杰也哉!
呜呼:感叹词,表感叹、惋惜(此处既有对范增“失势而死”的惋惜,也有对他“人杰”身份的赞叹),增强文章的情感色彩。
亦:也、也算(“亦”字表明,即使范增有“不早去”的不足,也不影响他“人杰”的地位)。
人杰:指人中的豪杰、杰出人物(古代对“人杰”的评价极高,通常指有卓越才能、品德或贡献的人)。
译文:唉!范增也算是人中的豪杰啊!
结尾升华:此句是全文的结尾,也是苏轼对范增的最终评价。苏轼在指出范增“不早去”的不足后,以“人杰”定论,既体现了他“不苛责古人”的宽容态度(开篇题解中“不苛责古人以全能”),也通过“呜呼”的感叹,表达了对范增“忠诚却遭疑、有才却难施”的惋惜之情,使文章在理性论述之外,增添了浓厚的情感色彩,余味悠长。
02金芬香:深究与鉴赏
范增为项氏叔侄所重用,献策定计,几乎是言听计从,但是最后还是因猜忌而分道扬镳,此事也导致了项羽最终的失败。在历史经验中,颇具有鉴戒的教训意义。
东坡此文,就范增的立场,分析其最佳的去就时机。古人说:"见机而作,不俟终日。"正是东坡“合则留,不合则去“的意思。《礼记·儒行》说:士君子是“难得而易禄也,易禄而难畜也”。这是说士君子辅佐明主,为的不是功名利禄,但是一定要得到人主的完全信任,所谓“得君行道”,以东坡的看法,范增显然得不到项羽的完全信任。
全文用的是论说文最常见的正叙法。首先说明历史本事,约举《史记》原文,作为立论的基础。其次则提出主要的论点,即指出范增应去的时机——“羽杀卿子冠军时”,全文以此为主,层层议论,总是畅发此旨。接着再以两段文字发挥此主要的论点,即宋义既死,范增必与项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,最后以去留时机与应所作为归结,和前面提出的论点遥相呼应。先叙后论,论而后定,可算得是层次井然了。比较特别的是全文虽然对范增未能掌握去留时机而多所责备,但归结于"增亦人杰也哉!"对范增还是有正面的评价。这种"恶而知其美"的褒贬方式,往往抑中有扬,扬中有抑,评价人物、论述事件,采取这种褒贬兼至的手法则比较公允。吕祖谦《古文关键》卷下所谓:“这一篇要看抑扬处!”即是此理。前人形容这种章法是“神龙摆尾”“临去秋波”,不是名家、大家,一般人是不容易做到的。
东坡此文有一警句,即“人必先疑也,而后谗入之”,一向君臣遇合,如不能推心置腹,总是最大的遗憾。范增与项羽的矛盾,不论前后发展有几个阶段,总以此项原因为关键所在。这种情形虽然是历史上的普遍现象,不一定只存在于特定的人与事,但是东坡一生几次遭谗被贬,乃至于他的死对头王安石之所以罢相,不能说不是人主轻信谗言、无法完全信任忠贞之臣的结果,这样看来,东坡此文也颇有借题发挥的意味。
宋谢枋得《文章轨范》卷三中十分推崇本篇,称:“一句一字增减不得,句句有法,字字尽心。后生只熟读暗记此篇,义理融明,音律谐和,下笔作文,必警世绝俗。”以无为有、绝处求生、抑扬有致、离合变化诸法之交相运用,使得本篇成为"词修而意远,深思极构"之妙文,的确值得诵读。
——张高评主编《古文观止》鉴赏,九州出版社
03汇评
[宋]吕祖谦:这一篇要看抑扬处,渐次引入,“难”一段之曲折。若无“陈涉之得民”一段,便接“羽杀卿子冠军”一段去,则文字直了;无“且义帝之立”一段,又直了。惟有此二段,然后见曲折处。吾尝论前一段平平说来,忽换起放开说,见语新意相属,又见一伏一起处。大凡作汉唐君臣文字,前面若说他好,后面须说他些子不好处,此论前说增不足道,后却说他好,乃放他一线地。(《古文关键》卷下)
译文:这一篇文章要关注它的抑扬顿挫之处,(作者)循序渐进地引入主题,尤其是“难”这一部分的曲折变化。如果没有“陈涉深得民心”这一段,就直接衔接“项羽杀死卿子冠军”这一段,那么文章就显得平直而缺乏波澜了;如果没有“况且义帝被拥立”这一段,文章又会显得平直。正是因为有这两段,才能看出文章的曲折精妙之处。我曾评论,前面一段是平铺直叙地讲来,忽然转而展开论述,既可见语言新颖且意脉连贯,又能看到(文气)有伏有起的节奏。大凡撰写论述汉唐君臣的文章,前面如果说他们的好处,后面总要提及他们一些不足之处,而这篇评论先是说范增(的某些方面)不值得称道,后面却又说他的优点,这是为范增留了一点余地。
[宋]楼昉:项羽杀宋义,便是要迫义帝,弑义帝,便是要去范增。盖宋义是义帝所爱,而义帝是范增所立,三人死生存亡去就,最相关涉。推原得出,笔力老健,无一个字闲。此坡公海外文字,故有老气。(《崇古文诀》卷二五)
译文:项羽杀死宋义,就是要逼迫义帝;杀害义帝,就是要除掉范增。因为宋义是义帝所亲近的人,而义帝是范增所拥立的,这三个人的生死、存亡、去留,关联最为紧密。(作者)能够推究出其中的根源,文笔苍劲有力,没有一个多余的字。这是苏东坡被贬到海外时写的文章,所以带有一种老练深沉的气韵。
[宋]黄震:增劝羽立义帝,使为楚谋欤,事成将置羽何地?为羽谋欤,又将置义帝何地?故羽欲成事,势不得不杀义帝,既杀义帝,则身犯弑逆之名,势不得不亡。增之拙谋,莫此为甚。而苏子以论增之功,既说矣,增实事羽为君,义帝不过增所假设以欺人者,乃谓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,力能诛羽则诛之,何哉?(《黄氏日钞》卷六二)
译文:范增劝说项羽拥立义帝,若是为楚国谋划,那么事情成功后,要把项羽安置在什么位置呢?若是为项羽谋划,又要把义帝安置在什么位置呢?所以项羽想要成就大业,从形势上看就不得不杀死义帝;既然杀了义帝,就背负了弑君叛逆的罪名,从形势上看也必然会走向灭亡。范增的拙劣谋划,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但苏东坡在评论中却称道范增的功绩,已经说了范增实际是把项羽当作君主来侍奉,义帝不过是范增用来欺骗他人的名义上的君主,却又说范增和项羽并肩侍奉义帝,(还认为范增)如果有能力诛杀项羽就该诛杀他,这是为什么呢?
[宋]谢枋得:此是东坡海外文字,一句一字增减不得,句句有法,字字尽心。后生只熟读暗记此篇,义理融明,音律谐和,下笔作文,必警世绝俗。此论最好处,在“方羽杀卿冠军时,增与羽比肩事义帝”一段,当与《晁错论》并观。〇论增只当杀卿子时,中间将义帝关楚关增处,实发得畅透,则杀卿子时当去,数语决之矣。又实先发弑义帝之兆,疑增之本二意,却俱于空中看出,必亦是发明义帝与增关系处。至接“方羽”云云,隐然在卿子上替他看出做手来。一篇文字离合操纵,警而活,如游龙之变化也。再反赞范增数句,别意作结,愈增全篇矫然之势矣。(《文章轨范》卷三)
译文:这是苏东坡被贬海外时写的文章,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不能随意增减,每一句都有章法,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心思。年轻人只要熟读并暗中记诵这篇文章,(就能做到)义理通晓明白,行文音律和谐,动笔写文章时,一定能写出警醒世人、超越流俗的作品。这篇评论最精彩的地方,在于“当项羽杀死卿子冠军的时候,范增和项羽是并肩侍奉义帝的”这一段,应当和《晁错论》放在一起研读。〇评论中说范增本应在项羽杀死卿子冠军时离开,中间部分把义帝与楚国、义帝与范增的关联之处,论述得十分透彻通畅,那么(范增)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就该离开的观点,用几句话就决断清楚了。(文章)又实际上先点出了项羽杀害义帝的征兆,怀疑范增原本就有二心,这些都是从看似没有直接关联的地方推导出来的,也必然是通过阐明义帝与范增的关系才得以实现的。到衔接“当项羽(杀卿子冠军)”等内容时,隐隐约约能从卿子冠军这件事上,看出作者对其中谋划的剖析。整篇文章在内容的分合、文势的驾驭上,既警醒又灵活,就像游动的蛟龙变化多端。最后又反过来用几句话称赞范增,以别样的意旨收尾,更增添了整篇文章刚劲昂扬的气势。
[明]茅坤:增之罪案,一一刺骨。(《唐宋八大家文钞·苏文忠公文钞》卷一四)
译文:(文章中)对范增的罪责评判,每一条都切中要害,令人警醒。
[清]储欣:论未确,而行文跳脱,不肯一字粘着纸上。(《唐宋十大家全集录·东坡先生全集录》卷二)
译文:(这篇评论的)观点不够确切,但行文灵活洒脱,不会有一个字显得拘泥板滞,仿佛粘在纸上。
[清]林云铭:行文曲折反复,无不入妙,煞是难得。末用数语叫转,更得抑扬三昧。(《古文析义》卷一五)
译文:文章行文曲折,反复论说,每一处都精妙入微,实在是难得。结尾用几句话扭转(前文的文势),更深得抑扬顿挫的诀窍。
[清]吴楚材、吴调侯:前半多从实处发议,后半多从虚处设想。只就增去不能早处,层层驳入,段段回环,变化无端,不可测识。(《古文观止》卷一〇)
译文:(这篇文章)前半部分大多从具体事实出发发表议论,后半部分大多从假设的角度进行推想。只围绕范增不能及早离开(项羽)这一点,层层深入地辩驳剖析,每一段都回环往复,文势变化没有固定的模式,让人难以揣测其脉络。
[清]余诚:大意只责增不早去,而以“羽杀卿子冠军时”句为主,人后层层议论,总是畅发此旨。然笔却极曲折变化,纵横离合,读者殊难遽寻其针线之密。〇开口以“去之善”一扬,跌出“恨其不早”。抑笔,人所易晓,至通篇俱用抑,而结处独扬,人几疑其自相矛盾矣。然须知通篇之抑,都是在“去就”一节上讲。结处之扬,就增为“高帝所畏”说,是褒增之才,故自两无妨碍。(《重订古文释义新编》卷八)
译文:(文章的)核心意思只是指责范增没有及早离开(项羽),并以“项羽杀死卿子冠军的时候”这句话为核心,此后层层展开的议论,都是在充分阐发这一主旨。但文笔却极为曲折多变,纵横开合,读者实在难以立刻理清其中细密的逻辑脉络。〇开头用“(范增)离开是好事”先作扬笔,接着转而引出“可惜他离开得太晚”的抑笔,这是人们容易理解的;至于整篇文章大多用抑笔,而结尾却唯独用扬笔,人们几乎会怀疑这是自相矛盾。但要知道,整篇文章的抑笔,都是围绕“(范增)去留”这一点展开的;结尾的扬笔,是就“范增是汉高祖所畏惧的人”这一点而言的,是在褒扬范增的才能,所以(抑笔与扬笔)自然互不冲突。
04范增论
【题解】
范增是秦末楚汉相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,历来对他的评价以同情叹惜为主,而此文则指出当初范增建议拥立义帝是为项氏家族笼络人心,后来又不能谏阻项羽杀义帝,实际上已违背初衷,其矛盾在项羽杀死义帝委任的卿子冠军宋义之时早已酿成,而范增“不知几”,不能及时离开,终致受猜疑愤恨而死。但作者也肯定范增是一位为对手所畏惧的英杰,不苛责古人以全能。
1汉用陈平计,间疏楚君臣。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,稍夺其权。增大怒曰:“天下事大定矣,君王自为之,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”归未至彭城,疽发背死。苏子曰:增之去善矣,不去,羽必杀增。独恨其不早耳。
【注释】
(1)汉:指汉高祖刘邦。陈平:秦末楚汉相争时,原为项羽部属,后投奔刘邦,成为汉高祖重要谋臣,并历任汉惠帝、吕后、文帝时丞相,封曲逆侯。
(2)项羽:名籍,字羽,楚国贵族出身。秦亡后,自称西楚霸王,封刘邦为汉王,在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斗争中失败自杀。范增:项羽的重要谋臣,曾屡劝项羽杀刘邦而项羽不听。
(3)稍:渐渐。
(4)赐骸(hái)骨:意思是退休回乡。骸骨,尸骨。卒伍:秦代乡里基层组织,这里指家乡。
(5)疽(jū):恶疮。
(6)苏子:苏轼自称。
【译文】
汉高祖用陈平的计策,离间疏远西楚的君臣关系。于是项羽怀疑范增与汉高祖暗中来往,逐渐削减他的权力。范增大怒说:“天下局势现在已经大定了,以后君王您自己看着去治理,希望您开恩让我这把老骨头回到老家去。”他回乡途中还没到彭城,就背上发毒疮死了。苏子说:范增走得对啊,如果不离去,项羽必定会杀死他。只是遗憾他没有早点离开。
2然则当以何事去?增劝羽杀沛公,羽不听,终以此失天下,当于是去耶?曰:否。增之欲杀沛公,人臣之分也,羽之不杀,犹有君人之度也,增曷为以此去哉?《易》曰:“知几其神乎!”《诗》曰:“相彼雨雪,先集维霰。”增之去,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。陈涉之得民也,以项燕、扶苏。项氏之兴也,以立楚怀王孙心。而诸侯叛之也,以弑义帝。且义帝之立,增为谋主矣。义帝之存亡,岂独为楚之盛衰,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。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。羽之杀卿子冠军也,是弑义帝之兆也。其弑义帝,则疑增之本也,岂必待陈平哉?物必先腐也,而后虫生之;人必先疑也,而后谗入之。陈平虽智,安能间无疑之主哉?
【注释】
(1)沛公:指汉高祖刘邦。
(2)几:微小。
(3)相彼雨雪,先集维霰(xiàn):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[插图]弁》。相,视。霰,小雪珠。
(4)卿子冠军:指宋义。卿子,是对人的尊称。冠军,指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,位在其他将领之上。
(5)项燕:楚国名将,项羽祖父。扶苏:秦始皇长子,被其弟秦二世胡亥谋害。
(6)心:楚怀王的孙子熊心。项梁曾立熊心为怀王。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后,又尊熊心为义帝。
【译文】
那么,应该因什么事情离去呢?范增劝项羽杀刘邦,项羽不听,结果因此失掉天下,范增应当在这个时候离去吗?回答说:不是。范增建议杀刘邦,这是尽臣子的职责,项羽不杀刘邦,说明他还有君主的度量,范增为什么要因这件事离去呢?《周易》说:“能根据微小预兆知道事情的趋势,大概就是神明吧!”《诗经》说:“看那下雪之前,先凝集降落的只是小雪屑。”范增的离开,应该在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的时候。陈涉得到百姓拥护,是因为他借用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名义。项氏的兴起,是因为立楚怀王孙子熊心为义帝号召人心。而后来诸侯反叛,是因为他杀了义帝。并且立义帝一事,范增是主谋。义帝的存亡,何止关系到楚的盛衰,也和范增的祸福密切相关。不会有义帝死了,范增却独能长久存活的道理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,是杀害义帝的前兆。而他杀害义帝时,就开始怀疑范增了,哪里一定要等待陈平去离间呢?物体一定是先腐烂了,然后才生出虫来;人必定自己先有疑心,然后才会听别人的谗言。陈平虽然聪明,怎么能够离间那不疑心臣下的君主呢?
3吾尝论义帝,天下之贤主也:独遣沛公入关,不遣项羽,识卿子冠军于稠人之中,而擢以为上将,不贤而能如是乎?羽既矫杀卿子冠军,义帝必不能堪。非羽弑帝,则帝杀羽,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增始劝项梁立义帝,诸侯以此服从,中道而弑之,非增之意也,夫岂独非其意,将必力争而不听也。不用其言而杀其所立,羽之疑增,必自是始矣。
【注释】
(1)关:关中之地。义帝派宋义、项羽救赵,而令刘邦攻咸阳,并约定谁先到达关中,谁就为王。
(2)擢(zhuó):提拔。
(3)矫:假托。义帝封宋义为上将、项羽为次将、范增为末将,派他们率兵救赵,宋义途中畏缩不前,被项羽所杀。
(4)堪:忍受。
【译文】
我曾经评论义帝,说他是天下的贤明君主:他只派刘邦率兵入关,而不派项羽去,他从许多将领中发现了宋义,提拔他为上将,不贤明能够这样做吗?项羽既然假托义帝的命令杀了宋义,义帝一定不能忍受。不是项羽杀害义帝,就是义帝杀掉项羽,这是不需特别聪明的人就能知道的。范增起初劝项梁立义帝,诸侯因此服从调度指挥,中途杀害义帝,这不是范增的意思,岂但不是他的意思,并且他必定是极力反对,而项羽不听从。不听他的话,杀害了他所拥立的义帝,项羽对范增的怀疑,必定是从这时就开始了。
4羽杀卿子冠军,增与羽比肩而事义帝,君臣之分未定也。为增计者,力能诛羽则诛之,不能则去之,岂不毅然大丈夫也哉?增年已七十,合则留,不合则去,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,而欲依羽以成功名。陋矣!虽然,增,高帝之所畏也。增不去,项羽不亡。呜呼!增亦人杰也哉!
【注释】
(1)比肩:并肩,意思是地位相当。
(2)陋:学识疏浅。
【译文】
在项羽杀掉宋义时,范增和项羽都处在做义帝臣子的平等地位,君臣的名分还没有确定。替范增考虑,有力量能够杀死项羽就杀死他,不能够就干脆离开他,这岂不是很果断的大丈夫么?范增的年纪已经七十了,和项羽合得来就留,合不来就离开,不在这时候明确是去还是留,却想依靠项羽来成就自己的功名。真是见识浅陋啊!话虽这样说,范增毕竟是汉高祖也害怕的人。范增不离去,项羽也不会灭亡。唉!范增也算是人中的豪杰啊!
相关链接
《古文观止》卷一1-18:《左传》经典选篇资料汇编合集
《古文观止》卷二19-34:《左传》经典选篇资料汇编合集
《古文观止》卷三35-45:《国语》经典选篇资料汇编合集
《古文观止》卷三46-56:《公羊传》《榖梁传》《檀弓》经典选篇资料汇编合集
《古文观止》卷四57-73:《战国策》《楚辞》经典选篇资料汇编合集
欢迎关注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富豪配资-富豪配资官网-股票配资怎么开户-在线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